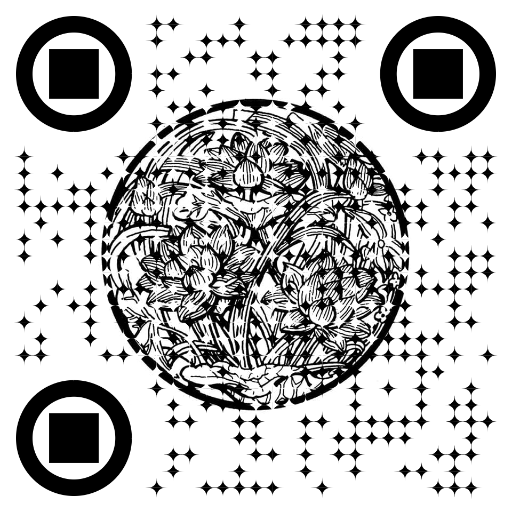南方的春常常喜爱金色结伴,潺潺流水出奇地熠熠生辉,石壁的一角,绿叶的一片,无不洋溢出沁人心脾的舒畅。要从溪畔不规则的石梯走过去,不管鬓如霜的老者,还是赤脚的顽童都要当心青苔使坏。
我的故居便是如此,看家狗狺狺狂吠,可吓的玩伴儿畏畏缩缩。一条土灰色母狗在对岸散步,一个疏忽,过不了多久落一地的小狗子。记忆中的它们无非是送人或是夭折。
说起春天,不得不提我家房屋后面的一颗樱桃树。它的身高和我一样不知道是否营养不良,不过运气好可以摘下果实来捧满双手,屁颠屁颠的跑回屋偷着吃。
离樱桃树近十步有一口水井,清澈见底。它时不时会给我带来惊喜,黑不溜秋的鱼苗让你两眼发光、成群结队的小虾米让你垂涎欲滴。如若是将至夏天那可是惊险之地,有虎钳大的螃蟹让你欣喜若狂。惊吓与危险就是无脊椎动物绕着井边,吐着蛇信子蓄势待发。不过我爷爷一个锄头下去就送它去了西天,一分为二的蠕动让我躲在奶奶背后瑟瑟发抖。
要说最有意思的事,插秧得排上号。自打我有鼻炎前,对气味过分敏感,乡村气息过鼻不忘。田地是从古至今农民的宝贝,哪户田多哪户生活就有了多余的开支。我家田不大不小,爷爷奶奶两人却有的忙。田野的气味是腥的,麦子是绿油油的,每个父老乡亲脸上是笑着的。他们穿好胶筒鞋踏进水田,佝偻着脊背,一个一个,一排一排的点缀色彩,像是莫奈那样的油画家,勾勒希望。汗水滑进眼睛便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然后继续工作......一直忙到蛐蛐叫才拎着背篓回家。
父亲是爷爷的儿子,却不似亲生关系。父亲和爷爷的性格如磐石不可搬也,父亲常年在外,鲜少回家。每次回到故里,父子两一言不发,奶奶多次调和却无动于衷。好比河里的蚌壳任凭水冲击誓死不张口。
契机是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一棵斜着的黄角树插在河畔,他不是粗圆的树干,看起来像扁体的木板,却厚实雄壮。有一天黄角树上冒出一个蘑菇,蘑菇像诱饵散发着诱人的魅力,我着了魔,欲攀,却幼小缺力。第一次尝到登高跌重的恐惧感。爷爷抛下锄头,眼疾手快,侥幸躺在臂弯上。或许是石板路不甘心或许是爷爷底盘没有稳住,一个屁股墩坐了下去,爷爷疼的咬牙切齿。父亲见状,疾速接过我。父亲劝其上镇上就医,可爷爷一口咬定自己老当益壮,小事无妨。
父亲是头一次,做出了让奶奶和我震惊的举动,他拉住爷爷的手,然后俯下身子驼起来,爷爷有点反抗,但父亲反锁起来,义正言辞:“别动!”。
随后,两位父亲在奶奶和我泛起的泪花里朦胧。
十五年后,我随父亲回到人烟稀少的故里。再次踏过小溪,干涸的小溪没了往日的风光,我望着寥寥的河畔惊叹:“之前的黄角树怎么没了?”。
父亲答:“好像因为河岸地基不牢移植还是死掉了,具体不清楚。”
父亲和我只有叹惋,陪了爷爷,陪了父亲,陪了我的百年老树化为乌有。
我愣在原地寒噤不已,父亲在荒芜的田埂前路回头催促:“快点!时间不早了,去给爷爷祭拜后得赶落日前回家。”
人与物都是瞬息万变一念之间,永恒的东西只有那份深藏在依恋里。长大后,我怕今后很难再目睹与体验乡间的春,便抠出模糊的记忆记录于此。
春色啊,固然妙。与您相遇,妙上加妙。
作者:李东徽
 首页
首页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