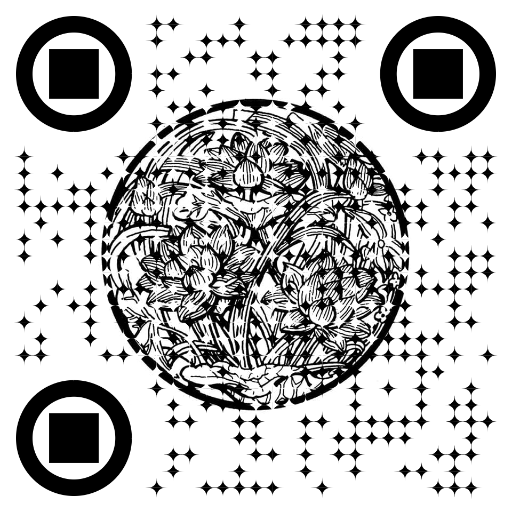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理论框架和战略部署,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重点是要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统一部署下,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多元化的实施方案,不必苛求全国乡村按照同质性的标准实施。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中,应注意坚守“五不”原则。
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
在农业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现代农业和资本进入农业的规模经营看作是农业发展的唯一途径,而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小农农业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且为农民家庭生活提供了生计保障。在现实中,由行政手段和资本主导下的“去小农化”过程将小农生产方式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残余”予以清除,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农业资本化动力正在加剧农村社会分化,小农农业经营方式被纳入资本化农业的低端环节抑或消亡。
应予以明确的是,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乡村振兴战略所力求实现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在坚持小农户和小农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平行主体地位基础上的有机衔接。因此,切不可通过行政手段或是鼓励下乡资本加速小农生产方式的消亡,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应给小农农业方式留以足够的生存空间。
在农村方面,长期以来“城市主义”的发展战略主导公共资源分配并持续吸附乡村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农村劳动力的抽离、“三留守”问题以及农村虚空的出现等,都值得重视。一系列以扶贫为名的产业项目或“公司+农户”的纵向一体化则将乡村再次推入自由市场竞争之中,而有些地方政府专于“造点”,乐于“示范”,使产业经营往往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脱嵌于乡村社会。企业只有在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才会以涓滴效应惠及农户;而在企业经营不善时,损失也常常由农民负担。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应深刻反思现行的产业推进和企业下乡举措,在坚守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享有产业链环节中的绝大部分附加收益。而依托“产业兴旺”的物质基础,以综合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环境治理和社会工作等活动来复原乡村活力,将是振兴乡村的重要行动。
乡村振兴不能盲目推进土地流转
在农地方面,有不少地方由权力和资本协力推动的土地流转以所谓“规模经济”和提高农民收入等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由政策文本和学术话语所构设的土地流转的农业经营规模效应并未出现,而结果却是大量土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究其原因,正在于资本化企业无法通过规模经营在种植环节盈利,因此它们力图在农业的上下游环节实现资本增殖。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化企业以“规模经济”为名推进土地流转,在农产品流通和生产环节排挤小农。然而,土地流转也无法完全吸纳原有土地转移的劳动力。基于劳动力替代型的生产方式,农业企业无法形成持续的雇工需求,最终结果是农民在“失地后又失业”。
因此,在“三权分置”和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尊重农民土地流转以及不流转的意愿,避免采取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或超经济强制的方式推进土地流转,应当是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特别重视的方面。
乡村振兴不能消灭农民生活方式的差异
在农民方面,继续探索适合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的长期有效措施,为老弱病残人口、留守人口等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障服务,是让国家发展成果惠及农村弱势人口的重要手段,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立场。
此外,乡村人口的生活方式既有与现代都市化生活方式连续相通的方面,也有其特殊之处。农民在维护社会稳定、食品安全、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要警惕商品化思维和现代化生活方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的过度挤压。
乡村振兴不应轻视基层的“三农”工作
在人员培育方面,长期形成的“贱农主义”形塑出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对“三农”价值的偏颇态度,与“农”相关的工作被视为低社会价值的事业,社会形成一种轻视从事“三农”工作人员的总体风气。因此,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应关注基层“三农”工作的重要功能。具体来说,应从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三农”价值导向的媒体宣传和深化农村农业价值教育的具体措施方面,开创“懂农”“爱农”和“支农”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战略应具有明晰的主线意识,并应与各种不当干预行为划清界限。乡村振兴战略回应的是“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议题,而这具体体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升级与实践方案的系统性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乡村价值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再次定位,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的不仅是乡村的振兴,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振兴。
文 / 叶敬忠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首页
首页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