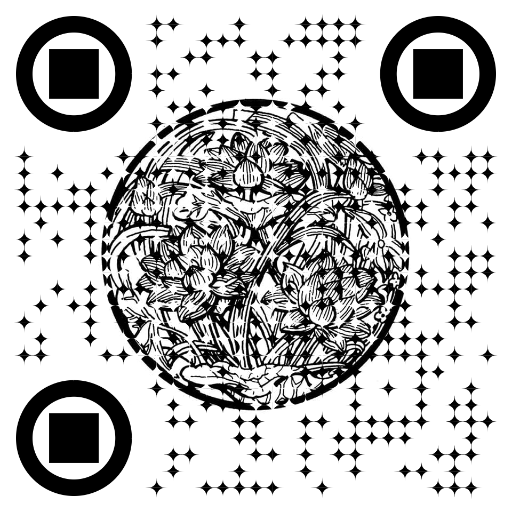文|王金世 董尚忠
当前,继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创新之后,又一项被人们普遍称之为涉及农村“四梁八柱”问题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分批次、按梯度陆续推进之中。为确保这项重大制度安排按国家规定和自创标准,做到不走样、不变形、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取得实效,现就前期承担国家第二批整县试点的泾川县、第三批整县试点的庄浪县和第四批整市试点的平凉市所遇到的几个瓶颈问题或潜在的制约因素,提出几点思考。
集体经济组织:一个需要精准认识的概念
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自其产生以来就为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支援国家建设乃至巩固红色政权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直到1982年《宪法》才有了没有明确界定内涵外延的法定称谓,2017年被《民法总则》赋予“特别法人”市场主体地位,实现了从法律地位到法人地位的过渡,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法律法规称谓不一,如1986年《土地法》的“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1986年《民法通则》和1993年《农业法》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等。虽然在改革伊始和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时,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原则和“设立乡级农业合作经济联合组织”的构想,但绝大部分农村“分”易“统”难,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尚未设立,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了徒有虚名的“空壳”,使其一起步就处于残肢跛脚的状态之中。在后来的历次乡镇机构改革中,对乡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构架、治理体系、资产属性均缺乏准确的定性定位,加之近年来一些地方或部门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时不时冠之以“村集体经济”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影响,致使一些基层工作者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属性混为一谈,不能准确地把握废改立、放管服的尺度界限,从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偏差,出现了个别乡镇领导越位干预甚至直接插手安排乡镇集体经济活动、审批乡镇受托代理村组集体财务,村支书或村主任平调集中、支配使用村内分属两个以上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侵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其所拥有的合法权益的现象,形成新的“归大堆”“垒大户”和“一大二公”等问题。
农户税费尾欠:一项需要统一解决的隐患
农户税费尾欠即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期间,因农产品阶段性结构性滞销、农村经济低迷不振、农民收入增速持续放缓,财税体制改革、分灶吃饭致使地方财力吃紧、养人压力加大、政出多门、层层加码、搭车收费频发,一些脱离实际的达标、评比、验收、否决以及让农民出钱、出物、出力的事项泛滥叠加,部分农户“钱、粮、宅、地、娃”一项或多项诉求一时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产生抵触情绪,拒缴抗缴拖欠部分或全部所应缴纳的各项国家税金和所承担的用于民办公助事业的统筹提留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迫于任务压力代交垫交形成的债权债务。从这次清产核资签字确认阶段来看,绝大部分为创收门路宽广、生活条件殷实、宗族势力较强的家庭所欠,而并非负担过于沉重无法筹资缴纳的农户所为,且总量超过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债权额的一半以上。为确保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和巩固改革成果,改革伊始国务院对农户历年费税尾欠先后做出“暂缓征收”和“是否清收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之后,除个别乡村借助掌管某项公权力对极个别急需办理相关证明手续的拖欠户采用“卡脖子”方式清收外,多数则因无省级决定一直暂缓至今。在这次改革股权量化阶段就有群众提出“若不是当年少数农户拒缴抗缴税费,集体垫支代缴,现在可量化的经营性资产会更多,应该彻底清收一并解决”的质疑。农户税费尾欠彻底清收缺乏应有的政策依据,继续暂缓有失社会公允,出现极少数人长期无偿占有集体资产无人问津的局面,并给基层日后实施一些民办公助事业留下隐患。故而建议从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指导性清收办法,以绝后患。
“三权”退出:一组需要审慎探索的课题
随着我国温饱问题的稳定解决,粮食产量连年持续增长,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非农就业门路逐年拓宽,农业农村确实已不再是农民唯一生产生活的出路,在出现大量农民进城创新创业落户,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现象的同时,一股唱衰农业、轻视农村、鄙视农民、非议农本,蛊惑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思潮也有所抬头(王健,2013),这既有悖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赋予农民更多更加实惠的财产收益,让农业成为最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职业,协调构建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战略构想,也与小农户家庭经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我国农业主要经营方式的基本国情相脱离,更与广大欠发达地区农民完全脱离农业农村所拥有的财富积累、生存技能、全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共保障服务等不吻合。加之目前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退出“三权”的政策与法律规定尚未明确,基层应对农户退出的接收时限、补偿计量标准、违纪违规处理之策缺失,特别是广大立地条件和资源禀赋差的山区耕地抛荒如何规划利用等问题都缺乏系统的处理预案,如何将进城农民“三权”有偿退出融入改革之中仍然是一项亟待规范的课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仅应该自己清楚“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走过哪些路、还该怎么走”,更应该明确地告诉每一位基层农村工作者和广大农民朋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一些福利待遇的载体,应审慎对待、切不可跟风盲从。因此,在新的征程上进一步广泛开展国民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一懂两爱”意识培养教育,尽快制定出台“三权”有偿退出政策和法律法规则显得尤为重要。
资源性资产:一类需要确立归属清晰的产权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自愿联合到政策引导再到制度规范,特别是各地为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本着兼顾有利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对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劳动力等资产进行统一调整,就近划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四固定”演变历程来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生产队即现在的村民小组,而并非是生产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且无论改革前后,在经济运行上二者总是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然而,在近年来由拥有行政审批权的自然资源部门完成的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发证工作中,一些地方为图省事而打破了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史界限,以村为单位确权颁证,这对清理核实集体资金资产资源,逐步构建以归属清晰为主的新的产权制度,充分挖掘利用各种集体资源,不断提升全要素产出率,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来说,除对已开发利用的耕地等资源性资产,可凭确已分属村内两个以上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长期使用的事实确权外,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尚未开发或亟待开发利用的“四荒地”等资源性资产究竟该由哪一级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使用,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引发了滥垦乱用无序竞争或抛荒沉睡无人问津并存的状况,制约了充分挖潜利用有限资源、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程。故而建议在涉及全国性农村改革政策时,应注意前后贯通、多规衔接,多一些持续完善、少一些另起炉灶。
股权设置:一道需要审慎选择的难题
改革开放初期,因绝大多数乡村对双层经营体制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致使新的农村经营体制从一起步就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之中,且不说农户从集体统一经营中获得的直接收益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家庭承包经营层次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中获取的间接收益几乎为零,就是后来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运转也全靠搭车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和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维持,以及为全面消除“空壳村”所付出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从我们所处的欠发达地区情况来看,目前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有的一点经营性资产是其组织成员进行统一经营、取得经营性收入、维持所承担的大量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开支和向成员收益分配的唯一抓手。然而在这次改革中对“是否设置集体股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定”的规定,再一次给集体观念本来就淡薄的农民群众留下了“分光弄净一点不剩”的说辞。若完全交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决定,势必会出现从“一分到了”过渡为“一股到了”的现象,使本已捉襟见肘的集体经济再次被掏空,保本增值、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愿望沦为无本之源的空想;若设置一定比例的集体股,多数农民因得不到实惠或漠不关心、或争吵不休,基层干部又怕违背上级精神,诱发新的干群矛盾,引起群众上访甚至群体事件而放任自流,形成新的极少数人操控集体经济的格局,使集体经济组织构建农村社会和谐的“稳压器”、促进乡村振兴的“蓄水池”、带领农民群众脱贫攻坚的“润滑剂”、促进新型产业发展的“孵化器”等诸多功能丧失殆尽。为此,在股权设置过程中,既要严格执行政策规定,确保政策落实不走样,又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在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和农民权利不受损的前提下,预留一定比例的集体股,用以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异地搬迁:一群需要持续关注的农民
异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标志性工程,确实破解了生产资源匮乏、生活环境恶劣地区治穷致富道路上“祖辈在治穷,世代老样子”的难题,走出了“年年盼着年年富,年年穿的没档裤”的怪圈,熔断了贫困代际传递的链条,点燃了他们与全国一道致富奔小康的梦想,激发了干劲、凝聚了力量,取得了“挪穷窝”“拔穷根”“摘穷帽”的目的,达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效果,夯实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它与易地搬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在保留其原有集体资产形态和资源属性不变基础上宅院住所的更换,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者放弃本来所拥有的资源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变价处理经营性资产及家庭财产后整体迁入新址,或者零星并入他村。在成员身份界定过程中,尊重历史、程序规范很好理解,也便于操作,而兼顾现实、群众认可就显得较为棘手,因为农村村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与一定生产生活区域相连的社会范畴,后者则是与一定资产相对应的经济范畴,成员身份是拥有与集体存在产权关系和最终获得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唯一标签和载体,是综合户籍、承包地和对集体积累贡献等因素后的产物,迁入群体虽在政府主导下取得了迁入地户籍,但因劳龄短、对原有集体积累贡献少,以及与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无土地承包关系而游离于村民成员之内、临界于成员与村民之间,在通过股份或份额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建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过程中,往往被挡在门外。为此,应尽量对移民搬迁户、出嫁女、入赘婿等特殊群体给予特别关注,充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以防他们再次掉队输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起跑线上。
古今中外、但凡改革,均以“破”始,皆以“立”收,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破”“立”,都会触及固有群体的利益,是一项需要慎之又慎、稳妥推进的难事大事,而并非说改就改、一蹴而就之事,就这项改革从零星自发探索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点,从中央纲领性文件提出到指导性《意见》下发,再到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足以彰显其复杂性、重要性和系统性。总之,改革犹如根治痼疾沉疴,绝非一味良药就能包打百治,但只要我们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严守原则底线、尊重群众首创、勇于实践探索,就一定能够打破“拙于创新”的谬论,建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既体现集体优越性又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新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农业经营服务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6期
 首页
首页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